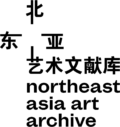一方面,存在着解码或解域的双重流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暴力与人工的再域过程。
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反俄狄浦斯 》1
长白山屹立在中国东北的东部与朝鲜两江道的交界处,在朝鲜称白头山,如同一个白色巨人在俯瞰着东北亚的辽阔疆域。从卫星图片的视角来看,在距今约260万年的第四纪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天池,如同一个深邃的黑眸,在向造物主发出“天问”。在漫长的地质时间末端出现的人类,靠山林的供养狩猎采集,靠火山灰化成的沃土播种深耕,在草原上游牧,在江河和大海边以渔获裹腹,在这方水土上一代代繁衍生息,根据“山川形便”建构起生活范围,依靠风土条件创造出习俗和文化。人们继而为宣称地权和治权而凝聚成国族,为争夺生存资源和文化征服而发起战争,这些无数的事件被诉之书写,便形成所谓的历史。而历史的积年层垒,加上文化的长期濡化,强化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把它视作自己的生存领地的意识,使它成了一个独具异质的人文地理单元,这便是一个结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
从遥远的地质时间推近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晚近年代,结域化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在他们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哲学著作《反俄狄浦斯》中,首次提出了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解域与再域可以理解成对历史结域的更替,它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以此驱动资本主义欲望机器的运转,同时也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出现。这两个概念后来也被应用于历史人类学对离散人群的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2 从家乡来到异地的移民,为了适应当地的生存条件,会逐渐放弃熟悉的旧的语言、习俗、文化与社会关系,而慢慢习得新的,并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而产生新的地域认同,亦即“日久他乡变故乡”。这也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解域与再域的过程。
结域化最初是作为一个界定国家领土和生存空间的政治地理学概念而发展出来的,3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发明了解域与再域这两个词后,地理学家们继续使用它们来建构区域主义(regionalism) 的理论,特别是城市更新实践在各地兴起之后,解域与再域这两个概念更成了分析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地产资本对社会关系的拆解重组的有力学术工具。4 而本次“长白之春”的驻地研究项目举“解域与再域”为题,则试图从文化和艺术角度,探讨如何打破人们对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更广阔的东北亚地区的刻板印象,在全球化导致流动性加剧和时空加倍压缩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论述这一地理区域文化的原生性(nativity)和土本性(locality),进而建构出新的文化主体和区域认同。
最早对长白山地区的地理测绘发生在1709年,由康熙皇帝委任的耶稣会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费隐是首次踏足长白山的欧洲人,5 他们使用经纬度测量绘制的地图被收入1717年以木刻印刷的《皇舆全览图》,可以说是大清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初次结域化记录。长白山绵延八千多平方公里,主脉为吉林省和两江道共享,余脉探向辽宁、黑龙江两省和朝鲜半岛,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豆满江)三条大河的发源地。它滋润化育的文化也从核心区推及辽黑二省、朝鲜半岛、内蒙古东部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形成涟漪式的圈层。它不仅是东北亚的地貌标志,也是这一区域文化生态的样本。
东北亚地区作为曾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和入主中原的大清政权的诞生地以及日本建立满洲国的拓殖地,一直以来备受历史学家关注;而这一地区所包括的中国、朝鲜、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领土区域,历来被视为活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观察点。但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主要聚焦东北亚的政治和经济维度,鲜有关心其环境生态、文化艺术和族裔社群方面的互动实践,“长白之春”项目正有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它的驻地位于中国吉林省一个朝鲜历史移民的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此处靠近天池,堪称长白山最核心的位置,项目以此为中心进行田野考察和研创活动,但其关注的视野覆盖中国东北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和学者们,在这个春天齐聚于天池之畔,共同探讨它的大哉问:我为何在此?我为人类带来什么?人类为我带来什么?
文稿:欧宁
-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研究中国明代卫所制度和垛集抽军法在福建的实施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了被征集到异地驻防的军户们的“日常政治史”。见宋怡明著,钟逸明译,《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 ↩︎
- 德国地理学家Friedrich Ratzel最早在他的Politische Geographie (1897)一书中提出Territory的概念,美国地理学家Thomas Sauer在此基础上丰满了Territoriality的论述,见Thomas Sauer,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参见John Harrison, “Networks of Connectivity, 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New Politics of City-regionalism”, Political Geography, Volume 29, Issue 1, January 2010, Pages 17-27. ↩︎
- Henry Evan Murchison James, The Long White Mountain; Or A Journey in Manchur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8), Pages 265-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