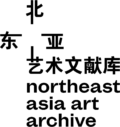受访:宋念申
采访及编辑:杨梅菊
作为打边炉和东北亚艺术文献库联合推出的专题“东北新声”系列访谈的最后一篇,我们对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宋念申的采访,多少带有一些“闯入”色彩。
宋念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人生的前二十九年里从未和东北发生过关系,直到21世纪初,他作为记者前往中朝边境采访,从此一脚踏入东北宇宙,再无脱身——那次采访后第二年,宋念申“误打误撞”转入历史学术的研究道路,而他在英国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将研究视阈投到了东北中朝边境之上,此后的学术道路更是不断卷入对东北的持续行走、观看和研究中。从高句丽和图们江出发,宋念申一边惊叹着现实的边疆与想象中如此不同,一边发现着边疆的流动和发散,他借助边境中具体的人、地图、皮毛或者街道回到历史现场,致力于描绘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意志力量搅动出的东北风云,同时也指认着边地和边地人的主体性……
将自身投入东北的成果和回馈无疑也是丰硕的,仅仅这个5月,宋念申的两本新书《发现东亚》《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陆续出版,而另一本新书也已准备出版。
巧合的是,就在我们采访前不久,宋念申刚刚前往中朝边境重走了21年前的那条路线。正是在途中,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告别之旅。自己对中朝边境这条线的研究,也许应该停在这里。他希望自己的学术目光能从东北边疆出发,投向更长更远的边地和更广的田野书写。
但无论书写的疆域扩展到蒙古还是内亚,宋念申深知东北仍是一切的起点。就像中朝边境这条路他走了无数遍,每次走仍能有新的感触和发现,而“接触得越多,了解得越深,东北就越变成故乡一样的存在,因为太近,反而不易开口”。说这句话时的宋念申,展现出整场采访中难得的感性时刻。而大多数时候,他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审慎、自持和严谨,迎接问题的同时,也破除着问题背后充斥的那些二元固化和智识懒惰,而面对争端和冲突、偏见与藩篱,宋念申希望寻求的是某种超越性——通过回到历史现场,在细微和复杂之处寻求现实的答案:不非此即彼,也不走向零和。而是潜藏在历史的孔洞之中的、一种全新的可能。
以下为打边炉与宋念申对话,按照惯例,本文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历史的现场
ARTDBL:你的学术道路始于对东北的深入和行走,但似乎又不曾把东北作为全部概念和对象,而是将其纳入到边界、东亚、东北亚欧等更广阔的框架中进行阐释,这种由点到线乃至面的研究思路如何形成?
宋念申:我的研究思路的形成,可能还是和我最初切入东北的方式有关:在对其没有任何感性了解的情况下,东北一下子就卷入到我的认知之中,从此被作为搅动东北亚区域局势的发生器进行观察和思考。
2003年秋天,我第一次到东北,以记者的身份采访朝鲜核试验对中朝边境的影响。在此之前,我既没有去过东北,也没有东北的概念,事实上那次的采访重点也不在东北,而在中朝边境,我接触了延边朝鲜族,并第一次进入朝鲜境内。所以等于我第一次切入东北,就不是纯粹的地方视阈,而是边界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我所看到的也并非一个完全静止和封闭的东北,而是边界内外的流动和切换。
这也是我误打误撞转入学术的一个起点,因为采访完第二年我就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到了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苦于题材的我恰好想到当时采访中了解到的高句丽争议。这个位于吉林通化叫做集安的小城,成为当年中朝争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焦点,背后牵扯到中、朝、韩之间非常复杂的外交纠葛,由高句丽文化遗产争夺所引发的东亚外交纠纷,就此成为我进入学术的一个视角。
当时所有的学者讨论的焦点几乎都是,高句丽到底算是中国、还是韩国(朝鲜)的,而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在1200年前,哪儿是中国,哪儿是韩国?我的想法是,如果要解决现实的困境,还是要回到历史中,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的态度和对这个地方的评价方式会发生变化,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把民族、国家的概念代入到地方区划中的。这个思路被我一直带到后来对图们江划界的博士研究里。
通过高句丽和图们江的案例,我才发现,原来东北这个地方这么有意思,对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的我来说,东北所呈现的边地要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具体到历史之中,你会看到更加错综复杂的盘根错节,而正是因为我们一味强调当代的民族国家属性,而忽略了历史现场的复杂性,才导致了至今仍无法用更超越性的视角去解决地缘矛盾。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案例出发,我开始思考该用怎样的目光去认知东北,开始意识到,也许不应该仅仅把它作为东北三省的地理集合概念,而是要放置在更大的概念中,去看到东北所处区域和全球格局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组关系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变化如何发生,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间边界的模糊性而非明确性。
ARTDBL:虽然是很偶然的契机,但是东北好像自此成了你后来延续20多年的学术线索,没有再离开过。
宋念申:说来非常巧合,就在两周前,我刚刚把第一次行走东北的路线重走了一回。唯一不同的是,第一次路线是从珲春出发,中间经过集安,结束在鸭绿江,这次则倒过来走,我们从丹东鸭绿江入海口以外的大鹿岛出发,一路开车沿江往上走,中间坐船探看了边境,在集安再次参观了已经整修得非常好的高句丽遗迹和博物馆,最后再开车到延吉,回到珲春。在路上,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好像是一次总结之旅。在开始研究这条边境的21年后,我想我可以move on了。当然作为一个题材,中朝边境这条线是永远有价值的,但事实上从学术层面而言,我已经离开它很久了,想一想上次到延边也已经是七年前。尽管未来我可能需要再一次回到这里,但我想这次重回应该标志着一次停顿——即使不是画下句号,也至少是一个分号。
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边界的,写书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其他论文也多是围绕边界,但随着现在英文学界关于中朝边界的书写成果越来越多,我想我可以暂时离开了。未来我希望自己的关注能够更广泛,不只在东北,而是涉及到更长的边疆和更广的地方书写,例如向蒙古、内亚的转移,起点当然还是东北。我想即便离开,东北的印记也已经非常深地打在了我对于整个东北的了解和叙述上,未来也会继续形成着我对边地持续观看的基础。
穿梭与流动
ARTDBL:在你的研究中,边地之人身体和身份双重流动性,以及对边界的反塑造被一再强调,这种对人在和边界关系中的主体性的指认,为何是重要的?
宋念申:我们对于边界的既有理解,不是依靠感受形成,而是通过现代国际法和制图学的所习得的概念。但当置身于边地,和当地人交谈,你能看到真实的边界并非那么意识形态化、那么有阻隔性。包括这次对中朝边境的行走,我也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一条铁丝网被沿着边界拉起来了,疫情之前,这里是没有铁丝网的,作为自然样态的河流、城市公园以及间隔排列的界碑发挥着边界的作用。
按照我们的理解,铁丝网的出现当然增加了边界的阻隔性,但事实上,在这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有什么是能被真正阻隔的呢?你能看到鸟儿依然飞来飞去,动物们穿梭自如。其实这种流动性为我们重新突破民族和国家的框架去思考历史和未来提供非常好的可能性。
要知道,现代边界的历史其实非常晚进,其形成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被塑造过程,进而成为理所当然的当下概念。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人在其中的能动性。拉了铁丝网,也不能够完全阻止偷越,不能完全阻止人在森林里的迷雾里走到另外一侧,而当一个家庭跨越两个国家,他们选择沟通还是不沟通,用何种方式沟通,这种选择反过来对边界产生形塑。我们会发现,不但边界跨越着家庭,而且家庭也塑造着边界。
我愿意把人所做出的选择视为能够突破民族和国家思路框架的新可能性,如果现有的边界概念,例如那些铁丝网、高墙和铁幕,是我们所能构想出来对群体行动空间或单元的唯一框定方式,那这个世界也太无聊了。我希望的是,当我们在理解这条边界,理解铁丝网,以及思考未来要保持边界还是打开边界的时候,能够有新的想象和可能的方案。
方向的矛盾
ARTDBL:你如何处理自己的研究愿景和铁丝网、高墙所构成的现实之间的落差?
宋念申:我不能否认这种落差。但我也明白现实不可能围绕学术的理想运转,现实本身是一个田野,而我的研究一定要在理解和反映现实的基础之上去提出愿景,我想我的很多写作期待的并非是立刻改变现实,而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止眼前这一种解决方案,我们有另外一种可能。今天的解决方式一定是应对了特定的危机或者问题,但这种问题不会在历史上永远存在,一旦有契机,改变就会发生。
另一方面,今天的现实一定是唯一的现实吗,大的方向真的一定是越来越紧缩、不往外走的吗?看似边界管控越来越紧密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和周边经济贸易、人员交往其实在强化,哪怕同样一个东北,中朝可能是越来越紧,但中俄则越来越热,所以你不能说紧缩和管控就是所有边界现实的样本。
再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上次去防川,我们只能去哨所边上的望海楼远远眺望铁路桥,但这次去就会看到,在哨所旁边修了一个特别高的叫“龙凤阁”的观景楼,同时延伸了一条离边界更近的栈道,修得非常漂亮,中间还有休憩的、主题性的小设计。当然这为的是吸引更多游客,是一个资本的逻辑,但是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三国交汇的边界做这样娱乐化的设置,意味着对流动人口的默认和吸引,这个动作至少说明,紧张性是在下降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是两个敌对的国家,会在边境线上修一条那么近的旅游栈道。
从这个角度来讲,边界被不管什么力量——资本也好、国家也好——打造成一个可以轻松消费或者休闲的空间,和20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空间的意义显然随着不同的时事发生了转化,产生了更复杂的意涵。所以我不会轻易下判断说,我们的时代大方向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方向的行进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学术所能反映的现实也是复杂和多层的,因此我们不能设定一个愿景,转而审判现实为何跟愿景不一样。
ARTDBL:似乎我们当前所讨论的收缩和紧张,更多指向的是中西方之间。
宋念申:即使沿着这个思路往前看,你也会发现,所谓中西方的线索也并非只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西方到底是谁呢?整个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很多的孔洞,就像边界一样。而人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这里,你是否意识到并愿意去寻找这个孔洞,去做一些事情。
吸纳和发散
ARTDBL:今天的东北尽管被主流看作失落之地,但依然接纳和收留着那些失意、边缘者,例如去鹤岗买房的年轻人,“脱北者”,这种收留与历史叙事中发配宁古塔的犯人、跨江开垦的朝鲜人、闯关东的山东人对东北的投奔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延续性,你如何看待东北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外来者们的关系?
宋念申: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在东北,到底谁是原住民,谁是后来者?你会发现,其实你找不到真正的原住民。因为东北就是一个多重族群或者多样生活方式的交汇处。那么多人来来去去,在这里建立起不同的部落、国家和文化,但没有人敢说自己就是东北的原生土著,哪怕满族人,也是从更远的地方迁徙而来。
与其他边地如西藏、新疆这些单一核心文明相比,东北这片土地上集纳了非常丰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有农垦,有森林,有集采,靠近蒙古西安岭有放牧,在外海又有捕鱼,不同的生活方式揉在一起,人当然就是流动的,边界是模糊的,肃慎族和靺鞨族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再到后来,一会俄国和日本人过来,一会朝鲜人过去,东北又成为一个枢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几乎可以说,东北人都是外来者,而所谓的原住民VS外来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好像不太适用于东北。
如果我们紧盯20世纪的脉络去看,会发现所有群体都在东北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满人,甚至还有迁居日本的台湾人,更不要说山东人、河北人……东北像是一个非常大的容器,容纳了我们今天所习惯的用政治学、社会学框架所区分出来的群体标签,这里一方面是吸纳,无论你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都能在这里落脚;另一方面则是发散,尤其20世纪,多个国家力量在这里展开及其复杂的竞争,而且所有国家都是以计划经济的形式,从日本到苏联再到社会主义共和国,都是国家大量投入去开发这片处女地,后来这样的模式发散到域外,引导出日韩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崛起,更不要说共和国时代,苏联许多工业项目的落地,又叠加日本遗留的工业化基础,这套经验发散到关内,东北对其他地方的援建也都是采用的这种计划经济方式。所以东北一方面是容纳外来者,另一方面又把20世纪的独特国家力量经验发散到东北亚许多国家,成为这个区域工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
ARTDBL:你刚刚谈到东北经验中国家意志的部分,那面对今天的困境,东北应该如何面对、处理自身和国家力量的关系?
宋念申:我想既不是继续顺从国家意志的叙事,也不是完全摆脱它,而应该是超越。这里的超越指的是一个超越性的逻辑,意即我们不需要在是或不是之间做选择,而是跳出选项之外看有没有适合东北的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逻辑看似一直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选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成功的模式,但当这种模式复制到东北,结果发现不成功。因为东北不是上海,不是深圳,它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轨迹都不在这个逻辑之中。东北本身有非常庞大的资源禀赋和潜力,对它的开发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式,而后来的经济转轨面临如此大的阵痛,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需要在两种模式之外看到第三种、第四种模式,而不是简单地说只要给政策、把图们江出海口打通,它就立刻成为下一个珠江或长江三角洲,这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从过去看,东北不是没有进入全球化,其实它已经接入了全球资本,只是没有办法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成为发展模版而已。
从边缘到中心
ARTDBL:所以回到历史的语境中,不同阶段下,东北在国家叙事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宋念申:其实今天的东北作为整体地域概念(而不只是东南部的辽河流域)被纳入统一王朝国家的直接管理系统,也就是从元朝才开始。明朝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在这里也只维持了25年,再之后就基本上实行式羁縻管理,所以从周边所有国家看东北都会觉得它是个遥远的边疆,但从东北出发去看,它一点都不边疆,而是容纳了各个周边地方影响的中心点,你可以从这里通往其他任何周边,日本海、朝鲜、俄罗斯、蒙古、中原……基本上东亚最重要的政治势力都在把它当作边缘,但正是这种处在多个文明或整体区划之间的边缘,让东北有了某种中心性,且导向它在历史上的功能和作用。只不过历史的叙事没有将其作为中心展开而已。
我们得到的材料要么是汉语的、要么是日语的,要么是蒙古和俄罗斯的,他们把东北处理成一个交汇点,但从交汇点本身出发,你会发现东北无所不至,所有国家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关国运的边疆组成来加以认知,这个视角的转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不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对东北有一个更有意思、更好玩的理解?不要一提到东北就是苦寒、没有文化、没有农业,其实不是这样,它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例如最典型的是清朝的崛起重塑了东亚政治格局,为什么会在这里?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东北的独特性就体现出来了。
ARTDBL:边缘和中心的二元性在东北是如何得到协调统一的?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宋念申: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资源和环境也同等重要。如果结合大航海和全球化来看,我们能发现有一些资源能够整个串联起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例如皮毛。大航海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寻找皮毛,西欧国家沿着北美河流例如哈德逊河寻找水獭毛,俄罗斯沿着西伯利亚河流寻找裘皮,后金努尔哈赤也恰恰是因为垄断了和关内的皮毛等重要稀缺商品的贸易才能迅速积聚大量财富。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中心和边缘的对立观点很难用来解释这些全球化中非常微小但又同时性的存在指征。再例如最近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汉学家卜正民的《价崩》,说到明朝衰亡的原因之一恰是因为小冰河时期带来的寒冷造成了物价和金融体系的震荡波动,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对皮毛需求的刺激,也间接导致了整个世界格局出现非常显见的、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侧同构性的巨变。所以从皮毛贸易的路径看,北美的皮毛和东北西伯利亚的皮毛都在去往中心地区,而这些中心地区则都在发生一些震荡,全球性贸易体系同地区的震荡就这么联系在一起。当然和北美大陆给欧洲带来的全球性链接相比,东北起到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但有相似之处。
ARTDBL:你所指出的作用,是否可以看作东北在历史线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对这种主体性的指认也是重要的吗?
宋念申:当然。我们做历史,一定是要给予那些我们过去没有太重视的所谓边缘、所谓底层,所谓不同族群或者性别,以更多的能动性。
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我们过去所固化理解的那些能动者去塑造的,历史其实是一个网,每一个族群在其中扮演的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尽管看上去起更大作用的好像是推动者这个角色,但是有时候被动接受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塑造整个模型的时候起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说,现代化就是欧洲的大航海家所推动的。如果没有西非的奴隶,如果没有那些北美的印第安人和皮毛,这些大航海家去干什么?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单向的线条,它一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或者是全球史,所有参与到网络里的社会、地域、文化,其实都非常重要,都值得我们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