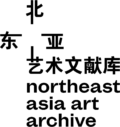受访:赵亮
采访及编辑:蓦然
五月的北京,我在赵亮的工作室外见到了他。阳光下他身形瘦长,眼神沉郁,站在那儿就像投下一片敏锐的阴影。疫情结束后,赵亮就不停歇地前往世界各地拍摄素材,四月底刚刚从巴西回来,六月又要启程去叙利亚。我幸运地赶在他停留国内的这期间前去拜访。
距离赵亮上次接受采访已有三年。对于我的到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矛盾:既有想说的欲望,又为内心想法的曝露而感到不安。这些年,从疫情到全球气候问题的紧迫,他越来越为人类行径里的种种荒诞而感到无力,有时也会自我怀疑,通过创作来改变现实是否真的有可能?
就像他所承认的那样,也许东北人性情里的直来直去的确影响了他的作品气质。无论是当年的《告别圆明园》(2006)还是《上访》(2009),激烈交锋的背后都是他手举一台DV,游走于制度和被制度所排斥的人之间,有时横冲直撞地介入,有时不顾狼狈地落荒而逃。这么做的背后,都有一种使命感的驱使。
那么这十多年间,究竟是什么逐渐让人无力?许多原因或许不言自明。尽管社会语境的变迁和个人视角都在变化,但赵亮并从来没有真正地动摇,只是越来越倾向于思考事物背后的一整套生产体系和历史机制。无论是关注鄂尔多斯鬼城现象背后的能源产业链,还是全球核灾难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视野和工作方式上的转变带动了他的美学呈现,让他的镜头从最直接的现场冲突往后撤了一些,但仍然坚定地在场,将鲜明的立场尽可能地杂糅到影像语言里。
他选择以狩猎的姿态,抓取他最能感同身受的那一部分现实。于是,在《悲兮魔兽》(2015)里,黑灰色的矿山和红色的井坑越是表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美,最后遍布空置楼房的白色鄂尔多斯鬼城就越是显得诡诞。在《无去来处》(2021)里,试图挑动反思的旁白贯穿全片,如鬼魂般萦绕在人类遥望废弃家园,或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室内舞蹈的时刻。
荒诞因此而无处遁形。至于那些在其中被异化的人,赵亮的镜头仍然在给予关照,长久地停留在煤矿工人脸上的沟壑和手上的硬茧,或是女人从沉默不语到悲悲戚戚的神情——既是一种爱抚,也是一种质问。
有时,人们会质疑他想传递的信息是否过于直接,从而消减了艺术上的余味,但也许是不自觉地,那股东北人的性情仍在左右着他的创作内核,让他拒绝过于含混和暧昧的表达。面对一个那么苍白的现实,赵亮执着地希望能带给你刺激和痛感,也唯有在当下身体力行地扛起摄影机和走四方,才是他坚定自己信念的不二法器。
我们以“东北新声”专题的名义与赵亮开启这场对谈,专题由打边炉和东北亚艺术文献库共同发起。以下是打边炉和赵亮的采访,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刺激
ARTDBL:你几乎没有在访谈里谈过东北,只在一篇2008年的对谈里提到一句:“做影像,其实是和人的气质有关系的……东北人说话不隐藏,心里有什么也都直接说出来,没有拐弯抹角,(我的)作品也是这种。”现在你依然这么认为吗?
赵亮:东北这片地域,可能的确养成了我作品里的一种气质。我心直口快,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些人觉得艺术需要有余味和留白,但我做纪录片特别希望能带给你刺激,就像一拳打在脸上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说是一种语言上的精准,或者是视觉上的冲击力,反正不是太暧昧的东西。我一直特别注重影片的视觉状态和语言转换。面对一个那么苍白的现实,我希望你看完了这部片子,它能让你记忆深刻,永远地留在你心里,而不是转头就忘了。
ARTDBL:作为创作者,那是追求一种非表达不可的感觉?
赵亮:无论是做纪录片还是做影像艺术,从来都是我觉得到了某个时候,自己就必须要做某件事、说某些话,我才会下功夫研究,用影像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从来都没想过商业的问题,每部片子的周期也很长。东北人的性情里还有一种,就是我不管别人,只做我自己的。但我还是比较追求一种存在的意义感。我会思考,这几十年来,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可能很多艺术家会觉得,追求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没有意义,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想到洪荒宇宙里,太阳系几十万年都没什么变化,大家好像都看得很透,像修养身心一样调整自己的作品。但我不是这样。我必须要有一种原始的意义感和动力,驱动我去做这件事。没有人生下来就全知全能,我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慢慢地观察和认识这个世界,直到我把世界的这个部分弄懂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学习。我也一直在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做作品,坚持用自己的肩膀去扛摄影机,从来不用摄影师。肉身抵达现场的过程就好像原始狩猎,本来摄影机和狩猎就有本质上的相通。我要尽可能地去抓取我想要的东西,回来把它们做成一锅菜,这样吃起来也比较香。当然运气也很重要,狩猎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
荒诞
ARTDBL:荒诞一直是你电影里比较核心的特质。早在你的第一部长片《告别圆明园》里,你似乎就有意识地在表达荒诞。
赵亮:并不是我主动去捕捉一种荒诞性,而是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荒诞,不需要我去刻意寻找。90年代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更多还是出于一种记录现实的责任感。DV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个福利,那时我拿着个小机器满街溜达,不需要跨入电影行业,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在圆明园画家村强拆时期拍的《告别圆明园》。当时圆明园一杆风来了要强拆,本来每个人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现在又要赶他们走,搞得人心惶惶。有一个场景是我在镜头里远远地看到有人来了,拿着摄像机就跟大家一起落荒而逃,还有人在笑,确实够荒诞的。其实那样的现场对我来说只有恐惧,没有兴奋,但我还是要坚持拍摄。后来拍《上访》,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应该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记录个人和社会现实的交锋。
ARTDBL:虽然《罪与罚》是在你家乡丹东拍摄的,但影片好像没有特别突出丹东的地域特殊性?
赵亮:我觉得所谓的地域性在影片开头用字幕交代,就足够了,因为那时的暴力执法不受法律约束,在哪座城市都是一样的。就像原来的北京抓盲流子,或者抓没有三证的人,还要用劳教、收容和遣送的说法。这几年因为有了摄像头的约束好了一些,但联想到疫情的时候,暴力也是突然地就这么发生了。有时我们处于信息茧房,一瞬间会不相信发生了什么事。但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观察人类行为,你就会相信许多事情都是人为的。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荒诞性,你愤怒也没有用。

欺骗
ARTDBL:关于荒诞,还有很多时候,荒诞和诗意在你的作品中是共存的,甚至会互相强化。
赵亮:好多人问过,我拍的那些景象应该是很丑陋的,但我为什么拍得特别美?其实本身看上去就特别美,只是败絮其中。我早年拍过一个摄影系列“北京绿”,当时北京为了盖奥林匹克中心,周边的区域全都在开发,盖上了大片的绿布,特别壮观,还有点中国传统画里的绿水青山的劲头。看上去是一种审美,其实是在进行一种现代性的反讽。《无去来处》里的原子湖直径有500米,水是碧绿的,看上去也特别美。但如果你知道那是原子弹爆炸后的结果,里面全是高辐射,你就会吓一跳。我在影片的旁白里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们对美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不自觉地呈现这种视觉上的愉悦感,如何欺骗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ARTDBL:你在《悲兮魔兽》和《无去来处》里想探讨的荒诞,和之前的影片相比似乎更具备普遍性了。
赵亮:这两部电影里的荒诞,更多是我主动操纵的结果,它很难表现为《上访》和《罪与罚》里的那种直接冲突,而是隐含在更长的时间线索里,或者说更广大的社会表象之下。就像现在,瑞士的冰川正在消融,当地政府为了减缓它们融化的速度,给冰川被盖上了一种毯子,可以反射阳光,让冰川多留存几年。但它同时也是个商业项目,允许人们进入在冰川内部打造的洞穴参观。这些都是一种人类行径的矛盾。去年,我回到《悲兮魔兽》在内蒙古的拍摄地,发现那里正在投资各种环境恢复的项目,又要在沙漠里种树,减缓沙漠化的蔓延,又要搞碳中和。但之前的开采已经把土地弄得乱七八糟,植被非常脆弱,原来的地表根本就恢复不了了。破坏很容易,重建是很难的。如果把目光再放远一些,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存在类似的荒诞情境。比如美国在70年代炸了那么多公共住宅,最近的新闻里,海南也炸了好多刚盖好的大楼。最开始都是出于利益,但因为缺乏长远的规划,再加上体制的崩坏,好好的东西就成为无价值的了。于是新的资金重启,谁又会成为新的获益者?

转换
ARTDBL:是什么让你从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转向影像语言的探索?
赵亮:其实我的所谓语言转换,还是得益于做录像艺术的经历。早期我在这方面的确做了不少,但其实直到1997年,我才听说录像艺术这个概念,原来都以为我做的就是一种短片。后来因为在纪录片领域投入的心血更大,就只是偶尔随性地做一些。拍完《上访》之后,我逐渐不再想做那种传统的跟踪式拍摄了,而是再进行一道转换,让影像更富有感受力、更深入人心。这是一个有深度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完成自我的过程。虽然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主义正在崩塌和削减,但对影像语言的探索,让我觉得至少还能坚持拍下去。这就回归到艺术的部分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形成自己的语言,才能让我的表达更加透彻。
ARTDBL:我觉得你拍摄人物的方式也在变得更加内省。
赵亮:以前那种拍摄方式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情感。因为我会进入每一个拍摄对象的生活,像谈恋爱一样地和对方相处好多年。但现在年龄大了,我会不好意思拍人。年轻的时候怎么都行,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拿着镜头怼人家,那种冒犯感挺强的。我逐渐也开始有距离感了,不太喜欢干预一个人太私密的部分,而是思考这个人的行为能怎么契合我的影片构思,抓取我更想看到的那一面。这也涉及到真实的问题,当然是老生常谈了: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作者为你呈现的真实。
ARTDBL:你会担心如今的主观性表达,注定要面临很多歧义和误读吗?
赵亮:确实有些人会对我的转变感到困惑。在一个行业里做了那么久,势必还是会形成自己在专业上的深耕轨迹。这个时代太油滑了,大家都学会了一种更快销、更流行的方式,可能是资本带来的浮躁。我还是特别尊重那种优雅的创作状态。但我还是会试着走一条比较中庸的路。我不喜欢实验影像这个词,也不希望我的影像是大白话。我更希望它像一座矿,深挖进去还有更多的层次,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层次和审美,能领略到自己不同的层面就好。我还是会坚持用自己的方法拍纪录片。其实我一直处于边缘的游离状态,没有真正踏入过任何一个利益圈的中心,但这不是抱怨,而是我觉得时代就是这样的,也有很多人选择了边缘的生存方式。
呼唤
ARTDBL: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你近年影片里比较核心的一种表达。是否从《悲兮魔兽》开始,你意识到人和自然环境的命运其实是一体的?
赵亮:人和土地、自然的关系是割舍不掉的,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恋情。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林区长大,去大都市并不能让我兴奋,但面对自然的丰富和美,我能感到无限的深情。这不是教育和政治能带给你的,而是一种本能。前段时间去巴西拍摄,村里的原住民带我去树林里转悠,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植物和香料,那就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种和自然的交流。我的确像你说的,特别注重人和土地的关系,也认同《人类世的资本论》这本书里写的,“工人和地球都是被榨取的对象”。但那些工人不仅被榨取和剥削,同时也是在自我消耗。你看那些煤矿工人的生活都非常辛苦,生存环境也很恶劣,但他们又确实是用自己的双手破坏、葬送了自然。我想通过一个局外视角,去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这里面的悲剧性都是我想要去批判的。再比如《无去来处》里,原本每到春天的耕种时节,福岛的农民们都会在田地里跳春耕舞,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农民被迫迁入到一个新建的社区,还是会在室内的公共空间里延续这种文化。但光脚踏在地板上的感觉,和踩在泥土上当然是两码事,所以我在旁白里也加了一些反思性的语言。我相信这些都会让人感同身受。
ARTDBL:影像这种媒介,在介入你所关心的环境议题时,能表现和放大的是什么?
赵亮:通过影像进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比如阿根廷艺术家托马斯·萨拉赛诺,他实施了一个针对生态问题的行动项目,但如果要有更多人接收到他的思想,还是要通过影像记录和传播,性质是一样的。你做了一件耗费资源、人力和物力的事,当然希望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就像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请了巴西的策展人和很多原住民艺术家,但这些作品的本质并不是在表达艺术,而是在借用艺术的外衣去呼唤世界,反思资本主义的进程和当下的冲突。所以什么是艺术?一个人利用艺术的工具,传达一种对当下或者未来更良性的影响,不就应该是艺术的使命吗?
ARTDBL:那么,你会希望在影片中传达一种你自己的主义吗?
赵亮:我当然希望建立一种自己的主义,但我的想法还很矛盾和不成熟。所以我现在更想去看看世界,听听那些真正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他/她们有什么意见?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太强大的理念。它带来了民主、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好处,但也通过对全球南方劳动力资源的剥削,盖起了自己的文明大厦,把全球变成了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基地。我也一直在想,这些年,都说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快速的发展,而是像有句话说的那样,等等我们的灵魂。但发展真的放缓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又没有得到关照。现有的主义太难以撼动,那意味着撼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应该有一种新的主义出现,让人回归和地球的关系,发明一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模式。
ARTDBL:现在在全球各地进行调研,具体的拍摄计划和挑战是什么?
赵亮:目前有一个七年的拍摄计划,但制作难度很大。计划的主要依据是全球气候问题,以及相对应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剥削。这里我会分几块,一个是全球各地的原住民的生存现状,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的,包括肉类、棉花、棕榈油等等,最后是工业,比如我们现在在日常中使用的稀有金属,例如锂电池,是如何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在国外拍摄不像在国内那么容易,你要了解别国语言文化,在当地找制片人,还需要有运气。你也很难在那些地方待上一年半载,只能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最后也只能是内卷自己,剥削自己,用尽量少的钱,自己多干点。
拉扯
ARTDBL:很好奇这么多年,你在悲观的现实和积极的行动之间,是怎么把握平衡的?
赵亮:有时候也会感到迷茫。社会在变迁,大家的价值感也分裂得很厉害,原来那种毫不怀疑做一件事的幸福感,包括那些影片里的批判色彩,放在今天的社会氛围里都被稀释掉了。尤其是现在去到了世界各地,看到了世界的纷繁复杂,以及不同地域的人们正在经历的荒诞,曾经那种想要改变什么的理想主义,逐渐会让你感到无力。你说这是我们在教育中得来的吗?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都会喊出和平的大口号,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却从来没有停止……但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的立场,只是不再像以前那么笃定地认为,我可以通过作品改造世界。虽然还是一直有想要改变什么的执念,但能改变什么,再说,至少这种信念还可以支撑我往下走。
ARTDBL:既然如此,拍摄对你来说意味着一种行动吗?
赵亮:我不敢说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行动,但我的确非常关注行动者,确保自己能把他/她们的声音也传达出去。我自己无法做一个亲历的行动者,在现场疾呼,但我相信作品的传播力可能是更重要的。我也是个环保主义者,会确保自己所有展览的材料都是可回收的,因为艺术家造成的污染同样非常严重。但我只是为自己拍。我很主观,要带着自己很强的目的性去做这件事。而且做纪录片最让我欣慰的地方,就是可以主动创造缘起。每到一个地方就好像结下了一个缘,将来再回到那里,我们就是老朋友了,可以在那片土地上深挖自己想要的东西。
ARTDBL:如今再回看早年的记录片,是什么感觉?
赵亮:每一段经历都是好的。如果现在让我拍《上访》的题材,我会拍得好的多,但在那时也算是完成了一种自我的建立。过去的经历塑造了我,让我一直被现实拉扯着,拍不了太高深、太乌托邦的东西。我觉得现实题材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对现实的关照,也永远会是纪录片的本质。在中国的语境里,独立纪录片的独立是相对于政权和宣传制度,但我认为真正的独立还是要有一种对时代的批判。这个时代需要直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