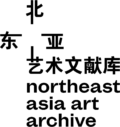受访:鲍大宸
采访及编辑:蓦然
鲍大宸在三月下旬从荷兰径直来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开启驻留。这既是他疫情后第一次回国,也是他头一回踏上完全陌生的东北土地。抛开了一切预设,他决定干脆顺应这份陌生感,也调侃自己总能被当地人一眼辨别出身上的南方气质。
鲍大宸习惯以行走的方式探索周遭环境。这是他在重庆生活实践了多年的经验。无论是在中朝边境、长白山上,还是朝鲜家庭的牛肉汤饭店,他感受到的都是一种浸润在日常中的民族叙事,如褶皱般层层展开。与此同时,我们的谈话也不可避免地在东北和西南之间来回折返,通过一种比较的视野,带出人与山的距离是亲密还是疏远,如何决定了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感知。
地方,既是鲍大宸多年实践的基础,也是这位年轻艺术家最近开始反思和警惕的对象。在过往的创作经历中,无论是深入重庆作为大后方的历史背景,还是由荷兰城市的变迁引出一段被遗忘的华人移民史,他都擅长以影像论文的方式在历史、档案和虚构之间游走。如今,鲍大宸期望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探索西南与东北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勾连。地处东北的边境地带也再一次提醒了他,所谓地方在社会和家国叙事的建构下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如何及时地做出应对和调整,或许是基于地方的艺术家所面临的共通挑战。
以下是鲍大宸的口述,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文中用图均由鲍大宸拍摄。

今年三月份,我到了东北,相当于是捕捉到了一个季节的尾声。从长春坐高铁到长白山的这段路程,沿路风景并不是想象中白雪皑皑的景象,但的确有一种后工业时代的落寞和苍茫。到了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感觉就像是重回小镇青年的生活。
相对于东北其他地区,在长白山区域还是能感受到一种多元性。首先是因为有朝鲜族生活在这里。驻地这段时间我吃得最多的就是朝鲜家庭开的牛肉汤饭,而且每次去我都会留意他们的日常对话,往往会在朝鲜语里夹杂着几个中文单词,他们的孩子就在一旁看韩剧。那种氛围会瞬间把你拉进一个异国他乡。另外,长白区域的自然感也更加强烈,如果去到长白县,无论身处何处都能看到远处庞大的山脉,这种感觉反而和我待过的重庆感觉更亲近一些。


我之前的实践,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一个具体的地方展开。但这两年我大部分时候都待在欧洲,无论是和国内的土壤还是语境,都已经隔开了一段距离。这次参与长白山的驻地,是因为我需要以一种田野的方式重新回到国内的现场,通过新的经验来激发自己的创作和思考模式。
一方面,东北这片地域可以追溯到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包括新中国的变迁、三线建设等,这让我觉得可以延续一部分过去在西南积累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东北对我而言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也的确是我第一次来东北。我想尽量避免带着研究的视角进入这个地方,甚至避免做过多的预设,而是通过最直观的肉身遭遇,看看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虽然我不是特别热衷于一种比较的视野,但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还是会不自主地在东北和西南之间寻找比较的线索。但比较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更多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地方和自己的联系。

比如在生态环境层面,西南和东北就有很显著的差异。在重庆,人处于一种被无名山环绕的状态,几乎每走两步就能看见一座山,人和山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但在东北,我觉得这里的山更具神性,人和山的关系也更有距离感。具体到长白山,可能和它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边疆和历史属性有关,山也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更强烈的象征意味。当然,对于那些每天进山的采山人来说,他们和山的关系又会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重庆作为一个山地城市,存在着很多的夹缝和褶皱地带,都是需要我通过步行肉身抵达的。所以这次来到长白山区域,我也理所当然地依赖于行走的方式,试着寻找类似的褶皱地带。驻地这段时间里,我不只待在二道白河镇,也花了很多时间探索图们市、长白自治县、珲春口岸、防川县等边境城镇。当然,这些地方几乎全部被开发成景点,在我拍摄的视频素材里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据说铁丝网其实是这几年才有的。

这次我还去了好几趟当地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可能是一直以来的习惯,无论去哪里考察,我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里陈列什么内容,陈列方式是怎样的。这些都会呈现一种当地居民和本土文化,以及大的政策方向的关系。在民俗文化博物馆,我发现满族在东北的历史和当地民族视角非常直观,几乎是无法回避的。这些都让我对有关民族国家和边疆的叙事很感兴趣。
但对当地的朝鲜族来说,这样的宏大叙事非常自然地浸润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人的日常消遣是通过专门的望远镜观看对岸的朝鲜,有时甚至不需要望远镜也能看到。我在行走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看起来非常魔幻的、有冲突感的场景,比如边境线这边的居民在用音量很大的音响播放音乐、跳广场舞,但对岸俨然是一副士兵驻扎的状态。

为什么我在创作中特别关注地理这一议题,其实和我之前在重庆的实践背景有关。在重庆,人和自然景观是一种非常纠缠的状态,作为艺术家,我们不需要刻意在创作中提炼这一点,也会不自觉地关注到自己和所处自然景观的关系。所以我也经常在想,如果说西南可以作为一种方法,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在看待人和物种关系,还是建筑和空间关系时,它都会赋予我们一种特别的视野。
另一方面,我对发掘所谓历史的褶皱也一直很感兴趣。在重庆,褶皱不仅在地理层面是可见可感的,也会让人联想到一座城市在现代性进程中被掩盖或忽视的灰色空间,或者说是一种草根的、民间的状态。但在东北的语境里,所谓的褶皱更像一种时刻,一种与当下拉开了距离、呈现出不共识状态的时刻。举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有一次我在二道白河镇边走边拍东西,一位正在河边钓鱼的大爷问我从哪里来,我说重庆。他笃定地说,重庆,四川省的。虽然这是个非常微小、日常的话题,但又的确代表着一部分当地人对东北以外的地方的认知,也把我拉到另一个现场,让我感受到某种断裂。


近些年,我的创作还是以影像论文为主,通过档案研究串联起不同的历史线索,再加上一些虚构的叙事,试图容纳多重的叙事角度。对我来说,这种研究性的工作方式仍然是必要的,但它也制造了一种坚固的创作逻辑和结构。一旦固化,就需要改变。过去两年在荷兰留学的经历,可以说是我把自己抛向了一个完全未知、陌生的地方,也让我不自觉地开始考虑自我和他者、自我和环境,以及创作和观众的关系。我开始希望寻找一种链接,一种认知或情绪层面的共情。折回到这次在东北的驻地,就像我最初说的那样,希望抛开预设和过去的创作方式,从具身遭遇开始。疫情后,从情感层面介入地方,变成一件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事。
这次驻地期间的拍摄,主要还是以记录日常风景为主。面对东北这种比较辽阔的风景,我更想要去拍一些具体而微观的事物,比如动物和植物,来体现一种差异感。除了影像,我也做了一些田野录音,可以听到朝鲜对岸的军事操练声,偶尔有一次,还听到一种会在酒吧里播放的靡靡之音,但不到一首曲子的时间就戛然而止了。


至于最终的成果,我可能还是会延续之前对宏大叙事和地方历史关系的探索,结合档案、实地拍摄和虚构叙事,讲述一个关于地方的故事,但也希望开放更多可能性,容纳一种相对抽象、模糊的状态。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陌生的经验,创造一种不那么完整的叙事?
我也一直在想,对于地方的关注,该如何避免陷入一种狭隘的区域主义。区域主义指的是一种孤岛式的、自上而下的、基于既定的地理和地缘框架而展开的一种研究和叙事方式,但艺术实践并不导向一种研究成果的产出,而是关乎于如何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替代性的联系。对我来说,档案和研究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我还是希望通过具体的创作方式,让这一过程隐藏在艺术叙事逻辑之下。

我会继续梳理这次驻地期间的拍摄和思考,也会试着寻找地方和地理间潜在的联系,尤其是地方和地理在民族国家话语下的亲密性,看看是否有可能发展出相对长期的实践项目,结合之前的工作经验串联成一个网络。这可能是一个听上去有些宏大的计划,但也的确是我希望从这次驻地开始尝试的方向。
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我总是会给自己设立一个假想敌,或者想象中的他者,而且是个大他者。我希望自己的叙事方式将是流动的,就像地方这个概念本身也在社会结构和国家层面的变化之下,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各方都在试图建立各自有关地方的叙事,来达到各自的意图和目的,这是一个有明显导向性的过程。作为艺术家,我在进行地方实践时,会提醒自己意识到地方背后的变化机制,及时做出一些调整。

出生于安徽芜湖,现工作生活于鹿特丹和重庆。硕士毕业于荷兰Piet Zwart Institute及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创作涉及影像、装置、表演和绘画等多种媒介,结合历史调查、民族志、虚构及故事讲述,审视地缘政治与生态、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结构性关系。近期实践主要关注川鄂腹地山脉,试图在物质性、具身及感知层面重新触摸、联系历史和记忆,探索本土性及多重时间性的纠葛,以恢复潜藏的另类叙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