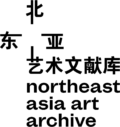受访:余果
采访及编辑:杨梅菊
五月北京渐热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余果。他来去匆匆,刚刚结束长白山驻留,返回重庆的途中短暂经停北京。
我们上次见,还是去年五月的798,余果在CLC画廊的个展《山脉之间》获得画廊周北京最佳展览奖,但这份荣誉并未令他更活跃一些,当晚的派对上,我甚至没听到他讲超过三句话。但事后知道,他一度为自己当时的沉默感到不安,这难免令人感到讶异:作为一个不善社交的人,余果显然无法强迫自己在特定场合扮演出某种纯熟圆融,但却会默默为自己的这份笨拙感到怅然——他遗憾的并非是自我的完整性无法得到表达,而是有人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适应不良而感到受伤。
所以与余果的交谈乃至交往也许必须是单刀直入的,去除冗余和矫饰的。正如这场采访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余果都显得如此拘谨和无措,但采访过程中说起驻留体验、艺术生产、工作方法时,他又是那么健谈、自在,如果试图为这种反差找到某种解释,我愿称之为社恐艺术家余果的自我有丝分裂。
而只有退回到自己的群山和田野中,余果才统一,同时完整。他的宇宙自有其构成:那些重庆郊野、山林里的漫游,新疆干燥的风和虔诚的诵祷声中的穿行,一路沿长白山所看到的移民、边界、森林与海……正是在一种近乎贴地的扎根中,余果不断试炼自己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和判断,并试图在系统内部寻找艺术生产的缝隙和孔洞。
在长白山期间,余果以位于二道白河镇的驻留空间为中心,将自己的足迹铺成一张尽可能向外辐射的大网。他租了一辆车,沿着长白山南下或者北上,从珲春到丹东,从图们江到鸭绿江,从一个林场到下一个林场。因为要省钱,他对行程的规划原则是最好当天返回,偶尔走得太远就沿途外宿,事实上,以成本核算对艺术所能抵达的范围加以规定,是余果一直以来的方法,或者说生存方式,他过着一种近乎低物欲的生活,对作品的商业化没有太多预期,但也并不将自己置于经济逻辑的对立面,他不焦虑大多数人的焦虑,但同时担心因为自己不焦虑而失去对眼下年轻人普遍焦虑的理解之可能。
作为一个悲观的长期主义者,余果的焦虑既不在眼下,也不生长于现实,而来自艺术之于时间的短暂和无效,他焦虑的是未来有一天自己再也无法对当代艺术和身处其中的自己进行分析或者发问。尽管更早的时候,他一度为无法找到进入艺术学术生产的那条道路而感到忧心,但后来,连这种焦虑也消失了——在弄清楚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在当初对趋势的预判逐一得到印证之后,余果反而更加坦然:他知道不是一切绝无可能。
以下为余果自述,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文中用图均由余果拍摄。

1
在长白山的35天驻留里,我基本上沿着长白山脉进行有限范围的移动。这次驻留之前我没有去过东北,对它毫无想象,因此可以说所到之处皆为未知,中朝边境,鸭绿江,林场,深山……看上去,这是我对长白山区域作为地理概念的探索和行走,但事实上我所见到的是远比这些概念要丰富得多的内容。
进入地方,需要找到一些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并接触当地人,他们中许多人热衷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希望带客户进山,虽然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后来我发现这些跑山的人或者他们的父辈、祖辈基本都是山东过来的,明末清初开始山东人就有闯关东的传统,现在看来这种迁徙今天依然还延续,尽管他们进入东北以及在当地生存的方式都有着变化。
2
驻留期间,我去了长白山的西麓,那里留存了很多当年小三线厂的废址,我突然发现当地人都说一口山东话,一问原来都是几十年前迁来的山东新移民。从这些人身上,我看到这些村落的兴起和湮灭,最初这里本无人居住,后来三线厂建起来,有了人居,再后来厂子搬走,留下空房子和废弃的厂屋,慢慢地就有山东人来到这里安居,再随着乡民口口相传,或者一些政策引导,山东人聚集得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个村落。我在珲春靠近中俄边境线的地方也看到,越是靠近两国交界的地方,人口就越稀少,山东人的村落也就越多,有些村子很年轻,可能两三年前才形成,有些早就存在但近些年也出现了大量的山东新移民。我到过其中一个黑顶子村,紧挨着边界线,翻过一座山就到俄罗斯,村里许多山东人也都是这几年迁过来的。当然除了山东人,也有河南人和其他外来人口,他们带来不同的口音与生活方式,但都在这里被接纳。
除了人居,不同的地形和生态面貌也很多变和杂糅,长白山看似从南到北,但山脉地区也并非连绵不断,南段谈不上什么农业,到了中段会有一些山间谷地和平地,现在会有一些蓝莓和西洋参的种植。再往北到了丘陵地带才有了玉米、大豆这些农作物的种植……再往北,过了吉林、长春后的平原湖泡地区,更适合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也是最符合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东北粮仓想象的部分。

3
就一个月的驻留时间来讲,恐怕远远无法抵达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深入,我做的只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走得再深一点,所以我基本不在驻留空间里长待,差不多都在外面跑。出去的话就想效率高一点,那边天亮得特别早,基本三点半就天色大白了,晚上六点多天黑,但我的作息并不严格按照日出日落,而是基于一种成本考虑,例如要提前规划,去一个地方需要几天,能不能当天尽快赶回,努力在省去住宿的前提下把在外面的时间最大限度拉长,毕竟车费、油费都是不小的开销,如果再加上住宿,那成本会很高。比如哪一天确定了往北走,我会一早出发,顶多在目的地住一晚,第二天结束后晚上开车返回,这样能省下一晚的开销。
好在驻留空间恰好是考察范围的中心点,从二道白河镇出发向外发散相对方便,基本上是这两天往北走一点儿,回到驻地之后再出发往南走一点儿,这样的工作方法说不上系统,可能更像是我一直以来的方式,那就是依据自己所在的空间及其客观条件进行一种基于地理的行走。
4
一直以来我都很期待各种进入具体的现实或地理空间进行创作的机会,长白山驻留算是计划外的一个项目,接到邀请的时机也很巧合,当时之前定好去非洲的驻留突然去不了了,而我又做了许多准备,那切换到另一个目的地对我而言有着同样的吸引力。
调研和田野是我近期确立的一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决定了驻留空间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资助,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相比过去那些一个人的独力创作,尽管也会形成作品,但不能说是非常健康的生产,加入驻留对我而言是当下比较需要的一种自我工作形态的更新。
去长白山之前,尽管对东北所知甚少,但仍抱有一种基于地方性的兴趣。我对大众文化、刻板印象乃至有意无意之中的所谓东北地方性的生产方式有着很大的好奇,这种好奇不存在褒贬,而在于对一种东北不同于其他地方性建构的关注。例如我们日常所谈论的东北,其实是很大面积的三个省,从地理环境到人文意涵都非常丰富,但为什么东北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叙事更为有效?它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为何又不来自传统和历史,而是在现代之中完成,为什么?而且这种叙事又如何借助大众传播或者娱乐化工业进一步实现自我的循环?我对这些感到好奇。

5
事实上,到了长白山之后我也意识到,驻留这一艺术生产手段本身似乎也成为了某种地方叙事的一环。
你去过长白山驻留空间吗?我认为它所蕴含的语境非常有趣,那个空间形态令人印象深刻:进门之后,一楼是特别大的工作室的状态,靠近门口的吧台上什么都有包括咖啡机、制冰机,打开冰箱能看到装得满满的各种饮料,从吧台向前几步是一排适合开讨论会的长桌,旁边分布着的沙发和茶几适合小范围的交谈,有投影仪、有隔离空间的天鹅绒幕布……
这个空间在我看来非常标准,是符合驻留这样一种生产机制的空间形态,进入的那一刻,我对驻地的想象、期待和假设都被实体化了,它代表了一套可靠的生产系统。
但同时,作为调研的一部分,我对这个空间也会有所反思,作为艺术系统内部生产的一环,所谓驻地的传统其实并不久远,但它非常主流,是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东西,相比之下,美术馆这种我们都知道的空间反而存在更多差异性,它会随着身处中国还是美国、投资方趣味和自身诉求而产生出无限可能,但驻地则非常标准化,对驻留者而言,在这样近乎统一审美空间内如何与地方发生关系,就变得更有趣。

6
长白山驻留我带了很多不同的拍摄工具,一些是新的,像网红们标配的大疆云台,也有用了很多年的手持DV,媒介是我一直敏感的部分,这次走长白山就发现,无人机这种看似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东西其实已经非常浸入当地村民的生活,去到每个村子和他们聊天,问起一些地理问题,村民们就会打开一个公众号,给我看他们村子的航拍,几乎每个村子都是如此,这种感觉很奇特,似乎那一瞬间你通过无人机这个媒介进入了村庄背后另一重空间语境,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
在长白山的西麓,我还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875分厂的冲印车间,8.75是胶卷的一个型号,同时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电影胶片规格,它相对于35毫米胶片耗片量更低,所以放映设备更加轻便,六七十年代农村地区和三线工厂里的电影放映基本都是8.75胶片的。今天看来,这个车间显然已经破败很久了,但守村的人带我去了审片室,这间审片室位置非常隐蔽,在当年的作用也可谓关键,长影制作的所有译制片、国产片,其后期反复审查都是在这间放映室里进行。
尽管守村的人告诉我,这间审片室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废弃了,但直到今天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虽然墙体看上去有些破败和陈旧,但空间所有当初的形态和格局都留存下来,没有被改造,也没有被挪为他用,像是凝固在了时间之中。这次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难忘,某种程度上875型号的胶片、那间放映室和我的行走、观看及拍摄都之间都有了某种隐秘的联系。

7
慢慢地,在行走中,我也不断思考如何将我所见形成作品,也许影像就是最便捷的方式,它不是话语,话语需要靠逻辑串联,但影像似乎更符合一种地理空间内的观看。
例如我在鸭绿江边就发现,在望向对面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显得很兴奋,这让我觉得好奇,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激动?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和朝鲜的接近都只停留在图像或者意识形态层面,但从未有过基于身体和情感的共情,它太神秘了,即使我们去旅游,看到的也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想让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但是我同时发现,那些架着机器直播的人、痴迷地望向对岸的游客们,他们所调动的想象几乎全部来自自己身后的世界。再例如夜晚站在中朝边境,看对岸一片漆黑沉静,转过头来就是这边恢弘的霓虹灯工程,那一瞬间很像置身1990年代站在深圳遥望香港,这种基于地理的观看,既是媒介性的,也是空间性的。
8
一个月驻留之后,我对东北没有答案,但有很多启发。这种启发可能也并不只关于东北,因为地理之间尽管有差异性,但我所想要追求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的思考是,一种文化生产如何去塑造一个地域?
我们对叙事的使用方式都是在不停的缝合和分裂之间。年轻时也许总会看到新的东西,很容易产生“自己正在面对新趋势”那样的兴奋,但现在会发现所有的叙事都有根源,而根源是缝合起来的,同时也在不断分裂出去。
例如刚刚谈到的中国人站在鸭绿江看对面,所调动的叙事积极性,可能比ta置身巴黎还兴奋,你会忍不住想,它的来源是什么,可能是我们对自身不了解之地所补充的想象,这种补充之中可能有三线建设时期大集体的经验、图像等等,这也是一种对分裂的缝合,是对叙事的丰富,但同时它也处在不断的分裂中,例如鸭绿江边直播者的讲述,其实是关于朝鲜女性和婚姻关系,他在那个时刻分裂的是自身的焦虑,是我们所在意的财力、阶级这些现实因素。这种缝合和分裂如此普遍,让我没有办法不从这个视角去观看和思考这个世界、不去做知识生产的分析。

9
刚刚说到地理概念的普遍性,其实这里需要一个语境,因为今天我们谈论地方性总是会期待它能提供一种特殊性,对此我不认同,所以才希望更多谈论地理环境所谓的共性。
地理环境之间当然有差异,山与海,河与谷,但这种差异同时也都同样来源于地壳运动,且之间相互关联,处于同样的一种运动和变化中。这里的普遍性,显然并非我们在日常话语层面所接收到的文化霸权符号——像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要么将所有现实存在予以命名,要么进行语义转换,或者像美术馆那样不仅收集不同之物,还要进行分类,有种一定要接受某种普遍性的强迫,但这种普遍性显然是不足的,屏蔽掉了很多地方性,导致了现在我们反过来格外追求特殊性,处处强调我们不一样,甚至想要输出某种特殊模式,非要定义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强调的共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撕裂性的思潮或者语境下,在对自我的身份或分化生态的过度陶醉下,所试图发出的回应。
10
从具体的感官体验上,身处长白山肯定和在我的家乡重庆不同,感受有它的尺度,自然会受到空间的影响。但从自身的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它一成不变,但总的趋势都是一样在生长。
在重庆不会麻木到没有能量,在长白山也不会兴奋得失去自我,地方经验的刷新或者再生都能给我滋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回避那些能给我刺激的新体验,中年之下能够得到突然的激发,当然是我所期待的,只不过在我当下的状态里,很难有突然的兴奋,因为首先我会质疑那种兴奋,相比之下,我更想保持的是一种循序渐进。

11
我做作品的速度不快,展览数量也不多,对市场也没有那么多期待,其实,无论在长白山,还是重庆,我都尽量维持一种低成本的生活。尽管也有一些生活的压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没有那么焦虑。有时候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会感觉到年轻人特别焦虑,我是无法充分理解这一点的,但同时也无法批评、责怪他们不够强大,客观上说,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多焦虑,可能我神经比较大条,脸皮也厚,没钱了就跟家里要点儿,没有那么强的上进心,也不被成功学叙事所强烈吸引,做艺术的这些年里,我基本上没有花太多时间解决焦虑这件事。
但这种不焦虑并不意味着我在拒绝或者对抗什么。我当然知道自己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别人,例如画廊怎么回事,拍卖怎么搞,成功的艺术家如何成功等等,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但也仅此而已,我既然了解了这些,那就更没什么好焦虑的。所以我对作品的商业化从来没有抱过期待,但也不会反感,因为对抗本身就已经在表达某种焦虑了,所以我也会挺质疑那种天天反对商业、不卖作品的表达,对市场说“不”其实很简单,但如果你真的不在乎,只需要默默转身去做别的就行了。
12
但我也有过自己的焦虑,就是一度对艺术学术的“求而不得”。我在乎学术,付出很多心力想要探究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学术,但学术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需要交流和异质经验的,我也知道自己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学术生产系统中,我期待一种健康的学术生产方式,可我并没有找到通往它的路径,这正是我所焦虑的。
当然现在已经不焦虑了,这个过程伴随着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了解的加深,和对更复杂的、多元部分的看见,许多事物都是这样,不了解的时候会非常焦虑,但一旦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你了解的所有信息都能成为你分析它的素材,你不需要印证什么,只需要去不断看得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这个适合你反而想要做一种全新的测试,而且怀着一种并不期待最后要达到特定结果的决心。

13
许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我长期待在重庆做艺术,会不会有点太边缘了,甚至是不是对中心祛魅的结果。事实上我觉得应该很容易想清楚这个问题——所谓当代艺术的中心或者边缘,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就像刚刚说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容易看清楚的,所谓中心还是边缘的命题背后,其实是人,及其ta的工作,艺术家也好,策展人也罢,我只需要看具体的人,和ta的成果就可以了,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人的不同阶段会彼此有所区别,某些话题有人关心有人不在乎,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搞明白它,并最终可以接受它,乃至接受当代艺术的全部,因此也就不存在赋魅,更无所谓祛魅。
这个过程就像田野调查,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方,当我对艺术生产感兴趣,那投身艺术的我自己也成为一个被调研的对象,反馈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理解这种反馈,例如某些时刻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无效?为什么除了我,少有人走在这条路上?当我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就不会有太多焦虑。
14
我本身是悲观的,但如果把目光放得再远一点,反而又稍微乐观一些,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我的很多最初的判断最终都得到了印证,整个趋势慢慢往你最开始预计的方向走,不是一切都全无机会或者全无可能,这是做艺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文化生产,最终还是不同关系之间的角力,这意味着艺术行业可能比其他行业存在更多缝隙,尽管它也讲究资源、资本等等很多不那么纯粹的东西,但都没那么绝对和唯一,你还可以有博弈的机会,例如当你没有资源,你是不是可以投入自己的身体去做?这样可能反而更自由一些,更有可能性一些。
但对我来说,可能博弈也挺没意思的,例如我不会把自己视为边缘,然后要和中心去博弈,这不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做艺术,并非再三思虑和权衡后的选择,反而比较被动:一是因为我不喜欢竞争,二是留在重庆更方便、成本更低。对我来说,它可以发生,这可能就是事情的全部。

余果,艺术家,工作涉及绘画、影像等多种媒介。目前工作和生活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