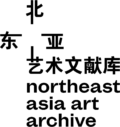受访:梁琛
采访及编辑:陈颖
作为中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单元,东北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这片土地的历史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的边缘位置,讨论东北,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边缘”与“中心”、“当下”与“历史”这些充满张力的概念。历史的影响力如同幽灵一般,无形却深远,它在这里不仅是过去,更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渗透在城市的文化和建筑里,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文化表达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东北新声”专题邀约的建筑师,梁琛对于建筑和艺术的双重实践,始于对长春和丹东城市空间历史的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地方性知识是当代知识生产所必需的情境,在逐步展开对东北地区历史与现代性的探讨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成长记忆,从家庭相册中的影像信息到城市建筑的物理形态,从个体的生活经历到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他对东北地区“历史幽灵”的多维度解读,探索着历史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显现其力量,以及历史遗留如何影响着东北地区的文化自觉。
初次认识梁琛,是在由他策划的鸭绿江美术馆2023年度的文献展上,其中参展艺术家葛宇路的作品《自然路径》里的一截地图,把丹东放了地图的中心位置,以东北亚为整体视角看待丹东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从鸭绿江防洪坝上移栽过来的爬山虎则沿着地图上的图钉自然生长爬行。这件富有隐喻和时间性的作品试图超越简单的历史叙述,突破历史的物理痕迹,这也是梁琛发起的“边界计划”实践中所要体现的核心,在梁琛看来,创造边界是人类的本能,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边界,都难以掩藏叙事的多重性,正是运动的边界所具有的开放性,让质疑得以幽灵般地存活。
以下有关梁琛的自述,是打边炉和东北亚艺术文献库联合推出的专题“东北新声”系列之一,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从出生直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丹东,后来在长春读了五年大学,直到24岁之前,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度过。不敢说对东北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我生命的比例上,东北的浓度还是蛮高的。
和大多数人一样,离开家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那里的关系,对丹东产生某种主观或作者意识,是在离开后的回顾中才逐渐形成的。至于所谓的东北意识,则是在长春的这五年里逐渐萌发的,这与我的年龄以及所处城市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与东北传统的工业城市如沈阳等完全不同,长春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城市。尽管城市规模不大,但长春的大学数量却很多,这使得城市充满了活力。在长春,人们常常会去书店或者逛长影(即以前的“满映”)的资料馆,这里的收藏非常有价值,我的电影史和影像相关的知识都是在长春获取的。我认为是长春启蒙了我对东北地区更深的历史认知,而不是我的家乡丹东。
我的专业背景是建筑学,而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就是关于长春的城市空间研究。在当时,我并未完全满足于传统的设计方式,因为我意识到城市的许多现状只是表象,我想从历史中寻找根源。这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影响了我,他从总体历史的思想出发,将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空间加以考察,这种方法启发了我,将长春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成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探究这个有限空间内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社会变迁。我想了解长春如何受到历史力量的影响,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塑造了长春的今天,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些能够说明历史原因的线索。例如,我当时发现我们学校的操场不仅为学生所用,还变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大爷大妈跳舞的广场。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长春城市规划的历史变迁,长春的城市规划曾由日本人制定,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原本的居住区周围都配套了许多公园。但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剧,这些公园逐渐被改建为商业用地,导致原本用于居住的区域丧失了日常休闲空间。
这段研究经历让我认识到,建筑学所面对的城市和空间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历史问题。只有深入理解了问题的根源,我们才能有效地介入和设计,从而解决这些问题。整个毕业设计奠定了我之后所有工作方法的基础,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当代艺术创作还是展览策划,我都有了一个空间史观的概念。无论是重新设计还是新的介入,都是基于对这个空间历史的理解,从宏观的城市空间到微观的小房间,这种工作方法都是相通的。
通常,建筑师更擅长在城市环境中设计建筑,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参考和限制。我曾负责阿那亚孤独图书馆项目的设计,在那种完全纯自然的环境里,没有任何人工语境,也没有明确的线索,对建筑师而言反而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大地艺术的概念和艺术家,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的。大地艺术的实践对我产生的影响和启发,甚至比建筑本身更具有持久性。我发现,不论是建筑还是艺术,实际上都是在介入某种时空,某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地方性的重要性,尽管我并不想将我的作品局限在某个地方性的范围内。有些人批评我说,我进行了大量地方性的研究,但我的设计语言为什么依然偏向数学式的抽象或简洁?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深入研究长春城市历史的同时,我也开始意识到东北地区历史的特殊性和有趣之处。深耕长春城市历史的过程,也将东北近代史的诸多问题,如伪满洲国、中东铁路等一一串联了起来。长春的城市和建筑的特殊之处,尤其在于它们展现出一种后殖民状态与现代现实的共存状态。例如,昔日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的建筑至今仍然被使用。我们常言建筑是相对永恒的艺术,因为它们较之能更长久地保存于世,甚至跨越多个世纪,然而,我对这种关于建筑安全感的观点持有怀疑态度。建筑一旦建立,它便具有了被改造的可能,无论是转变为学校、住宅,还是美术馆。但是,建筑的建造往往背负着政治的烙印,可能是殖民主义或皇权的象征,源自可能带有政治错误的背景。历史的包袱有时是沉重而复杂的,这种事实让我产生了对建筑艺术的纯粹性和永恒性的质疑。而如果这些建筑在政治上被认为不正确,那么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规划可能都需要重新审视和规划。当历史成为空间的幽灵,过去就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动态地存在于当下。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理大区,虽然面积辽阔,但其近代历史相对较短。在外界看来,东北三省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东北人一旦离开故土,往往只以“东北人”自居,这种地域认同是跨省份的。但实际上,历史的层次在这里依然清晰可见,尤其在伪满时期,“南满”和“北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南满地区,由于日本通过丹东和大连进入东北,因此主要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南满文化更倾向于日本的后殖民语境。而北满地区则因中东铁路在松花江畔的“T”字型交汇造就了哈尔滨,而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长春则位于南满和北满的交界处,作为一个中心地带,其地理位置和文化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了伪满洲国的首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辽宁人可能更偏向南满,黑龙江人更偏向北满,而吉林人则更中立一些。这些影响在今天可能不那么显著,但仍然存在,它们仍在建筑、城市规划、饮食习惯等方面悄然影响着东北各地。丹东作为一个例子,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着相似的饮食习惯,如生鲜和生吃刺身等,但东北北部地区的饮食文化则可能完全不同。东北地区内部的文化差异是存在的,靠近朝鲜边境的地区可能会受到朝鲜文化的影响,靠近蒙古边境的地区可能会受到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东北常被视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种印象被一些文化作品比如赵本山的小品、《乡村爱情故事》进一步加强。东北实际上是由三座山脉(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围夹而成的平原,分别靠近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内地,这些山脉不仅形成了自然的地理边界,也塑造了独特的山地文化。但是,东北地区的国界并非简单地以山脉的最高峰来划分的,而是依据山脉后面的河流走向为界,这种地理特点导致了东北地区边界的独特性。东北边境尤其特殊,它既是平原,又和东北内陆的平原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东北边境,这种差异性不仅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文化和历史等多个层面上产生影响。
我发起的“边界计划”,概念由疫情封控引发的思考而来,制造边界和消除边界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建筑本身也是创造边界的一种方式,从最初住进山洞,到搭建简易的遮蔽物,人类建造房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是建筑的本质。然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边界,都会形成多重状态。我策划过三个关于东北的展览,其中在南京金鹰美术馆的“作为中心的边缘”,是从丹东出发,深入关注东北的界河。东北的国境线由六条界河划分而成,丹东正是这些河岸城市之一。在这些边境地区,无论是村落还是城市,它们往往与对岸的聚落形成一个共同的中心。以丹东为例,虽然它位于中国的交通线路末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劣势,但边境城市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对岸的交流远超过与内陆的联系,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东北边境。这颠覆了一些人对边境的印象,那里并不是边境冷酷和世界尽头,我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境线上的城市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往往是因为它们与对岸城市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中心。
展览体现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展现出了丰富的层次感。实际上这些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在自己国家的边界内创作,他们之间的合作是跨越国界限制的,朝鲜艺术家可能会到中国来创作,中国摄影师也会去朝鲜拍摄,甚至有韩国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朝鲜的场景。这种现象体现了边界地区的特殊性,展现了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展览开幕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情况,有一位韩国艺术家非常关注展览是否有朝鲜艺术家参展和到场,在正式的场合上,他的政治敏感度甚至超过了朝鲜人,反而朝鲜人可能不太关心这些政治上的细节,但是在丹东,朝鲜族人、朝鲜人、韩国人就都可以共存。所以,边境看似是边缘,但它在很多的情况下会形成某种独特的场域,恰恰更为开放。
实际上,讨论丹东必然会牵涉到国家、民族和殖民史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日俄战争期间,丹东是重要的战场,日本的胜利以及随后的驻留,使得丹东相较于东北其他地区承受了更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丹东的铁路建设也可以说是东北地区铁路发展的先驱之一。殖民时期的影响宛如一扇敞开的大门,丹东的城市规划至今也保留了伪满时期的痕迹,这也反映了历史和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从丹东和东北的关系来看,丹东就像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出入口。日本人曾经从丹东进入中国东北,在战争失败后也从这里撤离。因此,丹东成为了许多涉及满洲地区的日本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比如冈田和裕的《满洲安宁饭店》,该书讲述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离的故事。丹东就像是一个关卡,被称为“东方的卡萨布兰卡”,许多人逃离东北时经过了丹东,以为到了朝鲜或日本,但实际上却是到了丹东。与此相比,黑龙江的满洲里也曾是俄国铁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这两个城市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角色上有着相似之处,都像是一个关口。
在我的创作中,谈到个人史的叙述,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这些历史,在丹东出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里承载的历史与其他四五线城市不太相同,对于丹东人来说,鸭绿江对岸是另一个国家,这导致了一种早期形成的他者意识或国际意识。地缘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比如《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杰克·伦敦在1904年就来过丹东,他曾以和平主义者的身份试图劝阻日俄战争,同时以记者的身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样一个边缘、偏远并且小众地方,却吸引了许多人来往,它实际上是比内陆对外交流更多、信息更为丰富的地方,比如在90年代,我的父母经营着日韩尾货的生意,包括开音像店等等,这使得我们接触到日韩流行音乐的速度比内陆地区快上一两周,我们基本就是听着什么HOT、EXO长大的。
对于家乡丹东的思考,是在经历了长春的研究之后,当我想要探究丹东的形成历史,乃至我家楼下的具体情况时,我发现自己对此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的空白激发了我深入挖掘的渴望。当我开始将个体的角色融入了作品中,布罗代尔与艺术家伊姆斯夫妇(Charles and Ray Eames)的作品启发了我,我开始在历史的时间中思考三个维度的建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其中,个人和记忆的维度即找寻个体记忆、经历和情感,我的方法是从家庭相册里的影像信息开始,以建筑学的知识来重构童年空间,这一过程中,我深入挖掘了大量的历史和材料信息,包括地面、墙壁、窗户、天花板和门等建筑元素的具体细节。这种唤醒很有趣,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触发一连串的记忆和历史,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从童年的房间开始,逐步扩展到我所居住的楼宇,再到楼下的街区,最终延伸至整个丹东城市的历史,形成了一层套一层的参照体系。丹东成为了我创作的原点,指导了我的建筑实践方法,这种逻辑关系很重要。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将对丹东的研究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乡愁,尽管这当中无疑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但它并不止于此。它与建筑界讨论的“中国性”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后者往往关联于中国建筑师如何在其作品中体现“中国性”。中国性也是一种地方性,建筑界的回应是,中国的木建筑、江南园林都是中国传统,但对我而言,丹东的生命经验里似乎没有涉及过所谓的中国传统建筑,我看到的都是大尺度的工厂、简洁的立面,以及现代化的网格化城市街道,我只能通过阅读、旅行去重新了解所谓的中国传统,但是它始终不在我的血液里面。进行丹东研究,我意在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起点。
在探寻个人与地域性的关联时,“东北”地理概念下的历史群体和文化特性也为我的思考提供了土壤。东北的原住民可能是满族或者更早的少数民族,现在形成的汉族大多是19世纪中期或晚期移入的,移民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过程,比如山东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东北人并不那么拘泥于规矩。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东北人通常会采取一种相互尊重的态度,也愿意为了不同背景的人放下一些规矩,包容共处。东北人对于文化扎根没有过多的执念,很少会看到祠堂等宗族文化的存在,与河南、山东、广东或福建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意识。东北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开放城市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比如广州、上海等城市,由于其口岸地位,早期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并且东北地区整体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因为铁路和现代化是同时发展的,形成了一个面和网的状态。
从昔日的后殖民地到国家工业的中心,再到改革开放后经历的变迁,东北的“落寞”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此深有体会。一个在改革开放受益的地方长大的人,可能会觉得,“咦,东北怎么这么破败?”但你会发现东北人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这种心态在东北的当代艺术家中同样存在。他们并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创作来表达,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当代艺术,都在探讨和面对这些问题,承认并消化着存在的落寞感。实际上对于东北人来说,即使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那些变迁,但父辈和祖辈都经历过了,一个东北的三代家庭基本上会很从容地消化这些经历。我曾与作家班宇讨论过这些话题,我们意识到,东北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地区的未来。中心化与边缘化的过程是持续存在的,东北可以被视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地方,东北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未来的人。当然,这并不是指确切的未来,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高密度变化、个人生活中的浓缩经历,以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苦难,如战争等,东北成为了一个时代和苦难的缩影。
这种环境必然会催生艺术,无论是文学还是当代艺术,都会形成肥沃的土壤。事实上,文艺在东北一直都是持续存在的。即使在伪满时期,文艺也没有间断,比如满映拍摄了当时中国最长的电影,总素材量惊人,当时也有独立的摄影杂志、建筑杂志、文学杂志、诗歌杂志等等,文艺资源非常丰富。东北虽然是边缘地区,但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它一直都处在边缘化和重新中心化的过程中。如果慢慢了解东北,你会发现它像一颗原子弹,是一个极为浓缩的存在。
在当代艺术领域,东北的后殖民情景其实是可以一直被讨论的,因为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还没充分意识到,日本在殖民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丰厚的史料,由于政治原因,中日双方都比较漠视这个问题,但韩国很愿意讨论,当然韩国有他的局限。关于东北亚的史料,文件非常多,在研究上具有文献优势,研究的空间也很广阔。对于东北学的研究,我认为从东北的日常生活出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规避了政治敏感性,一方面日常生活可以展现出真实的文化状态和人文景观,这也是东北文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于在东北亚成立文献库,是我期待的,在我看来,文献工作的扎实性可能表现在不仅包含公开发表的材料,也能涵盖尚未公开的资料。实际上,在过去短短的一百年里,东北亚发生了许多复杂而重大的事件,这个文献库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内部的资源,更好地保存和管理这些资料。我认为政策和审查的标准往往随时间而变化,具有流动性,而在我们进行工作时,尤其是文献工作,不能因为今天某些事情不被允许,就放弃了搜集工作,因为明天可能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去积累,最终就无法成为文献。我们需要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但也要考虑自我保护。我认为文献库应该是客观的,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可以选择暂时保留,而不是完全封锁。这样做可以确保长期的积累,避免碎片化的状态,以为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视角。